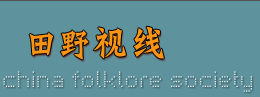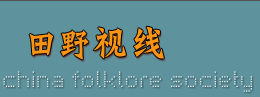|
引 言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进程中,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民间宗教和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是我们认识民众思想心理和行为规律的基本视点,广泛地影响和支配着民众日常生活,因此成为中国文化史关注的重点。民间宗教具有下列三个特点,(1)功利色彩强烈的神明信仰,(2)半制度化的教义和仪式,(3)非专业化的神职人员。后两个特点使民间宗教与不包含行为、仪式、制度的民间信仰区别开来,也使一些享受村落民众共同祭把的民间神祇有了界定性。它不包括那些无祭祀组织,无神职人员参与,不定期参拜的民间神灵,而特指享受共同祭把活动的神灵。本文所调查研究的村落神祇正是在此范畴内。
一、村落背景
本文所调查的地点安流镇位于粤东五华县西南部,居民都操客家方言。境内山多地少,现镇区下辖24个行政村,2个居委会,面积152平方公里,总人口约八万,91%是农业人口,主要由李、陈、张、胡、古五姓组成。
笔者选择这样的调查地点和研究对象,原因有三:其一,五华县作为纯客县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区域。安流镇村落神祇的形成和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客家民间信仰的形成过程,是文化地方化现象的体现。其二,安流镇各村落祭祀圈的分布很有特点。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区域内形成了李、陈、张、胡、古五大家族聚居在集市周围,杂姓小村偏居于边睡的局面,因而导致不同层次祭把圈的形成。它们显示了家族村落认同与神明崇拜的紧密关系,形式多样的庆典仪式为进一步探究民间宗教尤其是仪式方面的世俗功能提供了充分的素材。其三,神祇庆典的复兴是存在于当今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普遍现象,探讨其成因,对了解群众实际需求和心理变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协调各家族村落之间关系,解决民间互助、公益事业、个人得益等实际生活问题,适应家族村落内部分化又统一的权力竞争要求上,神祇庆典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说明了对民间宗教的引导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建立在合理、适度的基础上。
二、村落神祇的形成及其故事内涵
2.1村落神祇的形成
家族村落的生存发展总是和神明祟拜结合在一起。安流镇各家族发展情况也是如此。以李氏家族为例,从五华开基祖李敏公一世算起,传到如今已二十五世,约600多年历史。在李氏发展过程中,九世祖李撰(字顺之,号肖峰)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于“嘉靖十五年戌午科中试第三名”及第,初“授苍梧县志宰升广信府同知转升藩王府左长史”,1在族内可谓声名显赫,至今安流李氏仍尊称其为“状元郎肖峰公”。在他主持下,由第七世开始分支的“郁、实、草、广、通、盛、幼”七大房纷纷修谱,这就是安流李氏论及族谱时所谓“共八分九”的由来。李撰还邀请了当时一些名士为族谱作序。安流李氏各房派现存古本族谱中多有福建清流县人李可受之序。族谱记载李为进士出身,曾任广西梧州府某地知县。在序中,李可受曰:“长乐李氏乃一邑之望族,其十一孙曰撰编厥之谱,特以示予,求文以识之。”2可见,在七世至十世之间,随着人口的增加,房支的扩展,李氏家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家族村落的统一势在必行。在此时期,李氏七大房祖先祠堂得以建立,祭祀也得以大幅度强化。同时.蓝田蓝塘村修建了最早的李老君供庙,形成了独立的信仰中心,以此联结着周边的同姓血亲。
其他各姓族谱上也明确记载,陈万一郎、胡法旺、张法青生活年代大致相同,约在明永乐至明成化年间。在村民口碑中,他们成神都已有500年左右的历史,这和各姓氏家族聚落发展和分化的时期大致相符,基本反映出各姓氏向独立的家族村落发展时和神明崇拜相结合的历史过程。
可见,家族村落的认同是家族村落形成的重要前提。作为某一人群为某一共同目的进行认同的象征物,神和祖先担当起共同的责任。而神明崇拜比祖先祟拜有更大的宽容度,祖先祟拜一概排斥外姓人参加,而神明崇拜则允许外姓人共同介入。它不但能有效地调节各家族各房派间的关系,并能促进以地缘为基础,超出血缘范围的新的人际关系的产生。因此,随着家族聚落的扩展,为了村落的统一,神明崇拜自然被创造出来了。
2.2学法故事内涵:资源的争夺
在安流镇当地流传神祇的故事丰富多彩,其内容主要是关于神抵的来源。在神抵来源故事中,流传范围最广的是“茅山学法”故事。据说胡法旺公、张法青、陈万一郎三人结为“同年”,相协赴茅山学法。三年期满后都可以出师了。一天,师傅故意在腿上变了一个毒疮叫徒弟们吸。张、陈二人犹犹豫豫,胡见师傅疼痛难忍,赶紧上前把脓毒吸尽。实际上.“脓疮”是能使法力大增的仙药,所以,胡的法术比其他二人高明。三人下山回到家里,彼此间经常斗法,比赛谁的本领高强。类似故事在闽西、赣南客家村落中也广为流传。由香港海外华人研究社出版的《客家传统社会丛书》中,收集了许多这类故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客家文化的孕育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古代的福建、江西、广东一带,巫术流行。在当时,普遍存在着“尚巫”“俗重师巫”的历史背景,这是汉人、土著交融的结果。流传于闽西客家村落的“学法”故事和安流镇的
“学法”故事在情节上极为相似。故事主人公多是法师,隶属不同姓氏家族,几乎都用 “郎”、 “法”和数字来命名。他们生前是法师(巫觋),死后成为当地神。这些特点同样体现在广东少数民族尤其是畲族、瑶族文化中。“学法”的故事,“师巫”的习俗在畲族历史中可谓源远流长。畲族民间家喻户晓的“盘瓠”传说中就有着盘瓠投茆(茅)山学法的情节。3畲族隆重的祭祖习俗,相传也是为了缅怀盘瓠王赴茅山学法,不畏艰难的精神形成的。此俗之所以又称作“学师”、“传师”,是因为主持仪式的法师和学师者之间暂时形成了师徒关系,仪式的目的是为了让祭祖者获得战胜恶魔的力量,以免受人欺凌,“学师”实际上就是“学法”的仪式。瑶族也有“拜王度身”的法事,仪式目的和畲族的“学师”相同。度过身的要瑶人“始有资格当村长、瑶甲、师爷和取得法名或郎名”4。畲族瑶族都有以数字排行命名的习惯,这些都和客家先祖的“郎名”“法名”相同。象胡法旺、张法青,就是法名,陈万一郎则是“郎名”。舍瑶族人尊重法师,尚巫祟神,深刻影响了客家先民。一个法师变成当地一位祖先而被本地祟拜为神成为客家村落的普遍现象和信仰特点。
解读闽西、赣南一带流传的学法故事文本,可以发现,有一个情节十分重要和突出,这就是“斗法”。与主人公斗法的对手或者是精灵,或者是社官、蛇妖或者也是法师。
斗蛇妖的情节存在于年代较久远的斗法故事中,而且,蛇妖和社官往往混为一体。如紫金、五华一带流传的三奶娘斗社官的古老传说。5将学法斗法情节、尚巫学师之俗和百越土著民风结合起来考察,可以看出其隐约透露出来的汉族移民和土著居民争夺生存资源的过程和结果。许多史料证明,“人祭”和蛇崇拜曾经是百越地土著之习俗。“愚民无知,至于杀人以祭巫鬼,笃信不疑,湖广之风为甚。”6从民族学的角度考察,“斗法”实际上是不同移民群和土著部落争夺地盘、融合发展的反映。
安流镇的斗法故事是不同家族法师之间相斗的故事。据说胡法旺和陈万一郎最先斗法。胡邀请陈去赴墟(赶集),陈不去,因为他要起田(插秧),胡恼火了,便说:“我打赌你到曼(晚上)也起不了田。”陈不信,插完秧后不久他回到田里一看,见秧苗全被拨起堆放在田角。陈知道胡法术高明,只好甘拜下风,请他吃酒道歉。又有说张法青得罪了陈万一郎,到了年df晚,张姓家家户户点不着火,做不了年夜饭。有一个张姓人提着酒肉去求陈万一郎,陈对他说:“不怕,你点得着(火)。”此人回家后,果然点着了火。张姓人听说了,都提着酒肉去求陈。张不服,就去偷陈家鱼塘里的鱼。陈就写了咒语封塘,却把儿子咒死了,所以陈绝了后,没有传人。陈、胡、张三人斗法故事流传范围和家族祭把圈范围大致相符,各姓村民在讲述故事时,都极力渲染本族神明法术高强,神通广大。
安流镇村落神祇来源故事中,还有以下两类较有代表性,
(1)偷神像故事。陈万一郎神像原在梅林镇肖田寮村。安流镇增田村民陈某好赌。每次参加“花会”前,他都到陈万一郎神庙去烧香祈祷,次次都赢了钱。他便用布袋偷装神像回乡,放置在村中门墩下祖厅内设坛礼拜,很灵验。有一天神“降童”表示要在党塘、万塘村交界处陈光岭脚坐坛,于是村民们择吉时吉日,修起宫庙,从此香火越来越旺。
(2)捕鱼人捞神像的故事。学少村下小塘古姓一捕鱼人在河边打鱼,放下的鱼网捞到李老君神像,他把神像抛入水中,再放下鱼网,又捞到神像,连续三次都是这样。他便把神像拿回家放在柴房里,觉得家里开始事事顺利。别的村民听说也来给神灵烧香磕头,并集资建了庙。之后,李老君成了学少村所有古姓人共同信奉的村神。
在《客家传统社会丛书》中,我们经常遇到偷(请)神像、捞神像的故事文本,或者是一个赌博者或一个生意人去外地把神像偷(请)回家乡建庙最终发了财,或者是一个放鸭人或捕鱼人拾到灵物、神像,为它立庙祭祀而变得富有。在农业社会中,为了生存,就要不断为了好位置而竞争,这个竞争牵涉到所有的资源包括坟墓、祠堂和神庙那些象征性的资源。人们通过它们来把对手的利益压下去。神祇故事的作用正在于此。神祇故事是农业社会象征符号系统中的一员,是村落生存下去的另外一种策略。
三、祭祀圈的形成及其特点
从信仰范围,祭把方式来划分,安流各村落神祇主要有两类,一为护家神,一为众神。前者指一个同姓家族或几个自然村落共同奉祀的神灵,后者指不拘地域和姓氏共同奉祀的神灵。
祭祀圈是指一个以主祭神为中心,共同举行祭把的信徒所属的地域单位。本质上它是一种地方组织,表现了人们是如何籍着神明信仰来整合某一地域范围内人群的关系。从不同的组织原则来划分,安流各村落神祇形成三个层次的祭祀圈:(1)村落性祭祀圈,以村庙为中心,其形成原因主要是同村结合,即地缘结合。(2)超村落祭祀圈,以祖先神庙为中心,倾向于同姓聚落区的结合,即血缘结合。这两个层次祭祀圈所信奉神为护家神。(3)全镇性祭祀圈,以某一众神神庙为中心,成员自愿结合,居住地遍布全镇,大都彼此互不相识。
村落性祭祀圈则是指一个行政村或是属下几个自然村村民的结合,它反映出在村庄结合中,尤其是聚落群分散的区域内,地缘比血缘更为重要。比如蓝田蓝塘村,李姓占全村人口的80%强,分属三个大房,分别为幼公派、四房、六房,论血缘关系,幼公派和低坑祠堂坝李姓更为亲近,他们在明嘉靖年间十世祖枢公时才开始分支。而同居于此的四房、六房人由福陂一带迁来,为郁公派分支。郁公和幼公为同胞兄弟,是李氏七世祖。双方早在明前期就已走上各自发展的道路,只因幼公派先祖嗜赌,典地予四、六房先祖抵债,才造成今天三房混居的局面。但一直以来,三大房派都是本村神诞庆典活动的共同组织者。询问村中老人原因,都回答是因为路途遥远,不便和原房支合作。
另外,村里还有彭、谢、程等小姓约200人,也同样出资建庙迎神。在许多自然村落,由于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存在着血缘关系较为疏远的几个房派聚居在一起的情况。因此,地缘结合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在安流镇,超村落的祭祀圈有三个,它们是增田、龙中、万塘的陈万一郎祭祀围,洑溪、青江、东礼的胡法旺公祭把圈,半田、三江、福江的张法青祭祀圈。三位神灵受到区域内全体本姓族人的共同祭拜,每年神诞巡境日,人群浩荡,锣鼓喧天,远近闻名。村落性祭祀圈虽然规模上不如超村落祭祀圈,但在数量上较多,说明客家家族社会聚居形态的多样性、复杂性。而且,二者有着鲜明的区别:(1)村落性祭祀圈较小,一般不超出一个行政村范围,超村落祭祀圈则往往由几个行政村组成。(2)村落性祭祀圈村落多为单主姓村或复主姓村,超村落祭把圈则为纯姓村或或强单主姓村。(3)村落性祭祀圈地势较高,山地、丘陵绵延不断,交通不便。超村落祭祀圈恰恰相反,它们包括蓝田、万塘、洑溪、青江、福江、三江等平缓地带,紧靠安流墟市,商贸发达,交通顺畅。这说明,家族村落不同的发展态势导致不同形式祭祀圈的产生。
全镇性祭祀圈是一种松散的横向联合组织,具有自愿性、个人性特点。成员自由结合,不限家族和村界,每当神明圣诞便举行祭祀活动,俗称“会景”。庆典仪式较简单,既不演公戏,也不扛神巡境,更没有护家神庆典时家家户户大宴宾客的热烈气氛。这类组织影响力最小,尚不具备管理村落和区域事务的能力,作为信仰群体的特色还很明显。
全镇性祭祀圈和另外两类祭祀圈在成员组成上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首先,从会首、总理的组成来看,护家神祭把圈会首往往是由村中“长老”担任,他们多为男性,是所谓“讲道理,会说话,热心公益事业又有财力”的人物。总理则基本上由各“房头”的代表或户主担任,表现了浓厚的男性权威色彩。而且,一些会首、总理还和村干部一起,承担起村落的公共事务,小至兄弟妯娌争吵,大至村路学校的修建,都在他们牵头协调的范围之内。在他们身上,象征式权力和实际权力混杂在一起。“领导权力不仅是传统伦理风俗的指导,而且进入到地方公务的处理上面。”7而众神神明会会首,往往是“外来的和尚”。比如谢圣仙娘神明会,虽然庙宇位于万塘村陈姓人地域内,但陈姓人除了平时烧烧香外,一般不主动参与神诞活动。其会首多来自学园、吉程等村,大多为非五大姓人。总的来说,在护家神祭祀圈担任会首者,都不会去兼任众神祭祀围会首。大部分谋求此位者在村里地位居中。他们寻找的是一种象征性的权威。其次,从会员的组成来看,全镇性祭祀圈大都是妇女和家境比较不富裕的村民。他们只要交纳少少的一点钱,名字便可以登记在红榜上,张贴于庙门口告偷众人,获得一种“有面子”的满足感。另外象“仙婆嬤”
(巫婆),她们主要是为小孩子 “查关”消灾,为妇女“寻花”求子,并作召魂关亡之法,在村民心中,是让人畏惧又不屑的人物。在本村护家神诞上,她们只能作为一般的参与者,地位无足轻重,却往往受到众神神明会邀请,作为嘉宾参加庆典活动。
四、神祇庆典功能
各祭记圈在组织神祇庆典上都形成了一系列环节。一般在神诞前一个月,常任总理就开始召集村民筹备庆典活动。主要是通过会议的形式进行分工合作,安排各项事情的进度。神诞日举办的各种仪式也相对固定和程式化。
因为经济实力的强弱和成员组成方式等原因,众神庆典和护家神庆典在规模、时间上有差异。后者比前者隆重得多,一般持续2天,按顺序分为拜祭、行香、奉朝和做公戏、登席、巡游五个环节。
4.1神与人、人与人之间的象征
在调查中,笔者注意到,村民向神烧香祷告时,首先要把名省各府各县和邻村的神也一 起请到庙中享受祭品,再向神票明许愿者的住址、姓名、生辰八字和要求。如果必要的话,
他还可以通过“代神立言”的神童(当地称作童子)来得知神的旨意。庆典仪式中,觋公主 持的奉朝上表是最重要的环节。神明会从总理中要选派几人伴其左右,行三叩九拜之礼。这几个人实际上是仪式的见证人,如果因为疏忽见证人不在场的话,神明会就会拒绝向观公师傅支付费用。上表仪式比较繁琐,要到觋公将奏表念唱完装入封套内于神台前点燃才告结束。在蓝塘村调查李老君神诞时,笔者获取了奏表一份。在表中,觋公自称为臣,表抬头为:
“三天门下奉命臣×××诚惶诚恐稽首顿首奏,”结尾书:“谨疏呈奏以闻。”体例犹如古代官员的奏折。马丁在研究中国民间仪式调查材料时指出,“中国民间仪式雷同于衙门的政治交流过程,是一种意识形态交流的手段,具有自己系统化的符号与程序。”8中国民间神系——神、祖先和鬼——不仅象征一种等级,还代表了一个民间象征中的“衙门”
(政府)。人与神之间的交流,类似于臣子向皇帝上书,下级向上级汇报情况。在人们的想象中,神俨然成为替民作主的“官”。这反映出,在家族、国家权力中心之外,还存在的另外一个信仰中心,它同样拥有生杀取予权力,而且充斥着正义、道德、平等等观念,是民间对官方文本的交流,实则是统治思想的变异。
在象征化的村落内部与外部联系确认的同时,通过神诞庆典,村落内部的象征式“平权”也得到确立。这主要体现在村民的轮祭行为上。护家神祭祀圈总理一般都是轮流担任
(有一些村落有连任总理),或者由值年总理一对一推举产生,或者占卜由神选定,无论何种方式,基本每家户主都有机会当选总理,获得至少一次象征性的权威地位。众神祭祀圈会员也是轮流担任,每个村落约20个名额。每年神诞前,会首将请帖派到各村落某人手中.由他派发。在行香、巡游中,许多村落各小组行进的顺序则用“抓阄”的方式决定。
相对的“平权主义”还体现在神祇庆典费用方面。各项公共仪式花费来自族人的丁钱和乐捐。无论数额多少,神明会都会将乐捐者姓名写在红榜上,张贴于庙门口。家境富裕、社会地位高的村民总是会捐赠比一般村民数额高得多的钱款。他们的名字,往往单独大写在红榜的一边,而且,还能享受在会餐中被请为上座的待遇。村民们传诵他们的名字,对他们表示钦佩、羡慕。可见,他们和总理一样,也取得了象征式权威地位。他们的权威,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面子”,一种以金钱换取的“面子”。
作为多种象征权威模式提供者,神祇庆典是家族制度再创造的行为。它表现出家族与神之间的互动关系。
4.2庆典与家族村落的互动
神明祭祀必然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现,神祇庆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社会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其内部有什么规律,依照何种法则。安流镇不同层次祭祀圈运作过程显示出庆典组织和家族组织,地缘认同和血缘认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其中又呈现出整合、分化、均衡、斗争的特点。
神祇庆典的声誉和家族村落的力量成正比关系。村民在讨论时,焦点在于庆典办得热不热闹,好不好看。因此,反过来看,庆典成为家族村落“共利”和“团结”的必需品。它特具焙耀家族村落力量的特点,并造成一种群体认同感。然而,这种认同除了强调整体凝聚力外,还包含了家族村落内部的合作和分化两个层次,不同层次仪式反映出不同层次的认同感。
体现家族村落内部合作的典型仪式为“巡游”和“聚落轮祭”。在庆典仪式中,神像巡境可谓重头戏。村民们喜欢巡游时锣鼓喧嚣,彩旗飘飘,爆竹震天的热闹景象,但更关注神明的出游巡境。象欧阳村,偏居一隅,与万塘其它聚落相隔甚远,因此,每年巡游神明都不能光临其地。该村便于1988年自建六甲仙娘神庙,逢八月初九举办诞典,并将神像抬出神庙巡游全村,以弥补本家族神未能亲临之憾。
家族村落内部合作主要基于地缘认同。如蓝塘村多为李姓,也有彭、谢、程等小姓,他们同样信仰李老君。樟潭村赖、扬、朱姓都信奉慈悲娘娘。在大部分村落,即使是强单姓村,其组成之聚落由于家族内部的分化和迁移,亲疏关系变得相对复杂。利用血缘关系来结合人群的效用无法发挥,这也是神的威力为何大于祖先的一个原因。
然而,神祇庆典同时具备体现家族村落分化的血缘认同作用。在献祭、行香、巡游仪式中,这种认同表现得最为突出。献祭群体有“公”有“私”。前者指的是以神明会为代表的集体献祭,它表达的是社区的需要,体现的是家族村落合作的一面;后者指的是以房派为主体的献祭,表达的是家庭的需要,体现的是家族村落分化的一面。在拜祭仪式过程中,社会等级的差别也得以凸现。辈份高者排在祭队的前列,有威望者总是祭把的主持人,学问好、识字多的先生则充当“礼生”。在仪式组织过程中,家族村落“贵族”和房派“贵族”扮演了重要角色,长幼亲疏关系也得到了强化。在行香和巡游仪式中,每一个地方都是通过抽签来决定每支仪仗队的顺序。在名义上要求由一个村民小组组成一支仪仗队,但实际上,多数以每个房派为单位构成。可见,一方面,神棵庆典是一个以地缘为合作基础的地方共同体的集体性仪式,另一方面,这些集体性仪式由以血缘为纽带的房派组成。作为共同体内的个体存在和统一,不仅通过家族村落与外部联系得以体现,还通过家族村落内部的合作与分化得以确认,也就是说,庆典仪式不只是家族村落向外界炫耀的资本,还是内部房派竞争的资源。
神祇庆典还有助于建立民间交际网络,协调家族村落之间关系。近距离地观察神抵庆典,我们可以发现,它不仅是宴请本村神和其它众多神明,以答谢它保佑众生顺利,村落平安的日子,还是宴请村外宾客,联络彼此感情的时机。在村庙门口举行的“奉朝”仪式和在戏台上表演的“大戏”既是让神和本村人一起观看的,也欢迎外村人来凑热闹。神诞日在村中举行的宴会为家宴和村宴。赴家宴者多是姻亲,谁家客人来得最多,谁就最有面子。村宴则由神明会出面邀请别村有“有头有脸”的村民和总理们一起聚餐。
4.3庆典的信仰基础
民间宗教为家族村落发挥着维护秩序、团结,公共道德,教育等方面的功能。这些功能的产生,是基于对超人的神秘力量的崇拜。“这种观念是由社会和自然各种关系发生出来的。这便是相当于原始的各种关系和思维方法的世界观。”9古人认为,具备超人灵力的人、事或神圣不可侵犯的物无处不在,因而立下了种种不可违犯的“禁忌”条例。民间宗教通过对世界上存在着各种超自然物的假设来为人们解释未知事物和对付危机提供了“巫术观念和行为”。现代人也许不再这样畏惧超自然力的神秘性了。然而,只要人的需要还无法得到完善满足,“巫术观念和行为”就不会停止和终结。
在现代化过程中,随着机遇和挑战的增多,人们面临的社会风险也增多了。对命运的不稳定感,无把握感推动着人们向神灵顶礼膜拜,以获得免除人生灾难、疾病与不幸的药方。从心理层面上说,信仰“是人们有意或无意创造出来以供他们自己使用或满足他们自己各种需要的。”10人们去神庙,是为了解决他们的现实问题。中国民间崇拜的多神性已决定了民间宗教的世俗化,商品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又为它们进一步世俗化增添了催化剂。
神祇庆典本身就具有的功利性特点使它很容易在竞争相对自由的农村中转化为经济性的崇拜。改革开放以来,个人致富已成为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事实,利用经济实力来提高自身地位成为可能。一些经济条件好的村民成为村中有威望的人,他们是神祇庆典活动最有力的支持者。我到学少村调查时,该村神明会常任总理之一古某告诉我,“神公生日我们村办得最俏(好看,热闹),去走(巡游)的人每年都作一套一色的衣服。别的村没有我们的好。”口气很自豪。学少村民解放前就从事竹器编织,八十年代初成立了学少竹艺厂,产品销往国外,村民生活水平居各村之首。和增田村一河之隔的蓝塘村民说前者的神祇庆典“以前和我们差不多,现在不同了,他们村出了好几个包工头,有上百万,神公生日肯定办得好。”在调查中,我常常听到类似这样的议论,“以前他很穷。好在儿子生性(懂事),学会扎
(修)马达,在广州开了店,有钱了,年年是总理。神公保佑他家,生意越做越好了。”现代化的发展趋向使民间对商业利益的祈望越来越强烈,而商业竞争的加强又加剧了人们的振动和不安感。为什么人们愿意把钱花在神祇庆典上?神庙和庆典能够成为一种值得信任的文化传承方法,是因为有许多愿意为获得心灵上的安慰,精神上的保险而付出金钱的人在支撑着它们。
结 语
家族利用神明崇拜来培养群体认同感。不同层次祭祀圈在家族村落利用民间神明祭把来整合和分化地方社会上表现出了各自的特点和作用。家族村落的发展史是一部社会界限建构史。它强调家族村落内部的凝聚和均衡,强调家族村落内部与外部的协调联系,强调地方
“贵族”的优先状态,强调按照亲疏关系来结构人际关系。家族村落内部带有力量多元化的特征,多元化的力量通过公共象征的营造结为一体,也通过公共仪式的具体操作分别确立。
对于近年来民间仪式,传统信仰与宗族等传统社会组织的复兴现象,或者被归结为某些基层政权组织的涣散无力,或者被解释为官方“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政策导向造成。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家族历史的延续和家族村落不同社会力量协调的要求。神祇庆典成为了地方制度的一部分,持续有效地为家族和社区服务。
作为一个假想的权威,神灵是稳定信众不安全情绪的镇静剂。民间宗教复兴前提是社会变迁所造成的个人之间的差别由相对稳定变得剧烈起来,加上信仰的危机导致群众思想无所依托。如果不注重村民的素质教育,对他们的信仰引导老套、简单化,神明必然和愚昧结成亲密战友,共同占领人们的心灵市场。在新时期,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确实任重道远,不容我们忽视。
--------------------------------------------------------------------------
注释:
1、 五华李氏族谱理事会编印出版, 《广东五华李氏族谱上卷》,页243,1998。
2、 安流镇低坑村祠堂坝清光绪二十五年《李氏族谱》手抄本。
3、 施联珠著,《畲族》,页8,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
4、 李默著,《梅州客家先祖郎名、法名探索》, 《客家研究辑刊》,页79,1995年第1期。
5、 五华县文化局编印出版,《三奶仙娘学法》,《五华民间故事》,页2,1996。
6、 扬家骆编,《宋会要辑本》,礼二零之一三、一四,台北,世界书局,1997。
7、 吴暗、费孝通著,《论绅权》,《皇权与绅权》,页123,上海观察社,1948。
8、 马丁著,《中国宗教仪式和政治》,转引王铭铭《中国民间宗教:国外人类学研究述评》,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2期。
9、 江绍原著,《礼俗迷信研究之概说》,《江绍原民俗学论集》,页260,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10、江绍原著,《礼俗迷信研究之概说》,《江绍原民俗学论集》,页266,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摘自《民俗学刊》第一辑
|